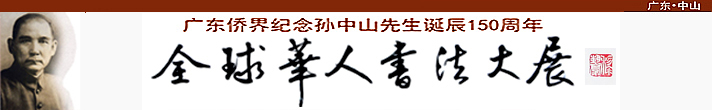简说甲骨文拓片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启示
●谭杰/中国文化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教育委员会副主任
上世纪末殷墟甲骨文的出土,给汉字书法引进了古老而又新奇的传统内容。甲骨文书法在当代书法创作活动中的展开,却长期处于尴尬的局面。国内各级甲骨文研究社团中兼擅甲骨文书法者并非少数,设若按书法本位标准衡量观,惟恐失之外道,介乎学者与书法家之间的集群素质游离边缘,步履维艰,究竟无法掀起巨澜。反观专业书法圈,亦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一般的作者仅偶为猎奇式的旁涉浅尝,有些可喜的探索性努力(如“少字数”书法、篆刻等等之于甲骨文的形式接纳)总局限于个体行为,难得打通出路,毋论再产生罗振玉、董作宾那样的甲骨文书法高手。相比之下,同属古文字系统的两周金文颇受礼遇和青睐。近世吴昌硕、黄宾虹以一代宗师出入篆籀,开拓变法并留下了大批优秀作品范式,已促成金文的创作在当代全国书法展览中蔚然成风。徐无闻教授藉中山王器独出偏师,也不乏追踵者。由是,自一度风靡的“甲骨文热”到浩如烟海的甲骨文书法实物载体——拓片,何以未能在当代书法创作方面显示足够的改造力量,亟宜深刻反思。理论研究的贫瘠和技术实践的脱节, 缺少专门立场的系统高度整合梳理,导致迟迟未能完成甲骨文书法与大书法文化传统的科学承接,长期滞于“学问的婢女”的地位。事实上,对甲骨文文化实施分科研究,势必破坏部分原始神秘感,它为我们置换得到的即关于创作方法 论的新启示,既是甲骨文书法的,又牵动其它书体的现代审视。
汉字书法作为服从视觉的一种审美形式,首先面临的是空间问题,空间问题通常涉及数学和物理学。巴洛克时代微积分的独立发明者莱布尼茨认为:“音乐是灵魂在不知不觉中的算术。”音乐空间的展开仰仗听觉与脑图像之间复杂的抽象转换,理论上可倚靠技术螺旋趋近之,譬如巴赫对十二平均律(人为地把一个八度按等比级数分成十二个相等半音音程)的控制与娴熟运用,几近完美地展现了严谨和谐如公式般的数学美。空间问题在当代中青年书法工作者中也引起了广泛重视,有人试图刻意借助自然科学的原理分析过去我们自以为熟悉的那个传统,结果令人兴奋而恐慌——我们原来对传统的了解竟至如此肤浅粗陋!
商代甲骨文书体面目繁多,董作宾依据风格演变大体划为五期,此外尚有朱书、墨书、周原卜辞系列资料待考。上古先民无须任何理论准备,问占鬼神的敬事心理自动外化为集体无意识的审美及技术追求。试选取一些各具代表性的拓片分析为例:线对空间整饬有序的分割正是主观把握的结果;某些笔画端点和弯折处的处理,已出现成熟的技术;单字主要取狭长造型,局部或作相对于正位的偏移,常态连接、非常态连接同构模型;字内空间被挤压程度与章法疏密存在天然的辩证关系;横向平行直线的视觉可延展性进一步规定了字间距小于行间距,得到开放空间;弧线围合梭形,得到封闭空间;分界线的使用(应是出于卜辞文字内容的需要)间接打破局面,与前述空间感受相反,似乎暗含了后世的隶变的基础;不少直接根据板块特征分行布字,空间演绎为均衡式、密布式、渐变式、辐射式、散点式……丰富的空间层次奠定了汉字二维构形(独立成形或分组成形)的建筑美,通过行侧廓线、单字(字组)外接多边形、夹角情调等可大致判定风格归属。有的字形省略、归并、黏粘、挪移,以后的书法史上能够找到近似情况:汉简、残纸的片断偶合现象可能表明仍未脱无意识状态,至北宋黄庭坚一变,其作大草书多采用邻字穿插、嵌入,略见人工痕迹。明代中期祝枝山出,夸张黄氏点法,增益直线,大胆造险,作长竖每斜势疾下推进,存心留出补空位置给下一字,段落衔接机巧太过则露俗态,不能不说是失败的努力。这条路线后经倪元璐、黄道周等人走到极致,字里行间呈强烈反差,满纸敏感促迫气息。以苏轼行书充当参照,一种看似木讷甚至无动于衷的处理反倒收获了天真无饰的效果。历代书家口授心传“计白当黑”的重要经验在此得到印证,字内、外部空间的形式单元意义,丝毫不亚于线构的。
视觉空间的数学构成,有赖于时间的作用,时间带来运动问题,即物理问题。当作有限载体的拓片折射反映无限世界,到处都充满着相同性质的直线和弧线,非周期、随意而有机地交替分割空间。将拓片信息中单字轴线、字组二重轴线、整行更为复杂的轴线集合(若即若离波动于中垂线左右)做一逻辑分析,视之为后世帖学“行气”的滥觞谅不为过。甲骨文书法的线运动是不完全连续的,据郭沫若先生考证,镌刻顺序应为先竖后横。主笔有序反复,辅笔虚变不乱,形成各种错综、交织、覆盖的节奏:短节奏与长节奏、均匀节奏与律变节奏,也许还有情感律动。甲骨文书法的节奏研究始终和当代创作息息相关,一切变化均由空间中的主导元素——线运动的几何轨迹决定。
据此,人们是否可以纯出主观,想像单凭科学计算就设计完成一件尽善尽美的艺术杰作呢?当然不行。中国书法是带着镣铐(汉字字形、笔顺的硬性法则)跳舞的徒手线,而不是几何线。尽管我们无限动用几何原理分析任何作品,但是作品本身无论结字、章法还是点画,都完全不是几何性质的。有古人现成的反例——蔡襄书碑《昼锦堂记》为证,此碑“每一字辄书数十择其合者存之名为百衲碑”,单挑结字个个无懈可击,通篇格调却“失顾盼之神”。这里恰是忽略了书法创作中至为关键的“贯气”问题——孤笔不成势,孤字、哪怕孤行也不成势。楷书尚且如此,脱离了具体的书法语汇环境,“择其合者”根本无从谈起。节律决定笔势,笔势产生瞬间表现力,每一根线都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创作者在书写过程中对空间不断关注,随机调整生发。所有企图违背时间秩序者从最终效果上看必定吃力不讨好,这一特征跟乐曲演奏颇为相似,否则书法就堕落成为工艺图案。米芾《珊瑚帖》“珊瑚”二字的骤然放大,王铎在一些草书作品中故意错位字间连带的落笔搭接方向,乃至不惜违背自然过渡规律追求突兀的淡浓枯润,上述无妨看作矫枉过正的观念抵抗。形式规律的奇变手段未来可以发展得更加充分多样,平衡不可能简单地解释为平均,有时非要打破某处局部的平均,从而获得视觉心理的平衡享受,“不和谐的局部”成了提起全篇的“眼”,还是属于整体平衡的一部分。
当代书法理论一旦触及最精微处的空间、时间、节奏的解构,总会造成更接近技术而与艺术内在精神南辕北辙的负面印象。然而只有经过了客观冷静的分析加之大量的书写实验和练习,创作方能散怀抱,不至于在技术点上层出疏漏。理性与灵感、激情决不是水火不容的矛盾体两面。相反,经历压抑之后突如其来的的创作冲动,往往更具不可遏制的生命暗示意义。观念“不及格”,脱离了高级层面的技术支持,“十年苦功”式的临摹对书写水平的提高并无建设性的用处。更多时候,“灵感”、“激情”容易沦为一种自欺的、炫奇的、单调的习惯性唤起,经常主动沉溺其中,无疑于创作是有害的。
现在,研究者们已经逐渐认识到,完成从原生态到演生态甲骨文书法的创作转换,由此顺藤开拓一些新的研究课题,乃是时代赋予之大任。甲骨文多为直接镌刻,墨迹极为稀罕,只好关注拓片,因而想像力发挥余地较为广阔。完成转换的条件有二:一是拒绝步趋原本。瞻观先贤罗振玉的作品,其做法最大程度地还原原作笔墨效果,保留书写意味。实际上,还原是不可能的,除了需要对付宣纸、毛笔等材料工具的特性,具体到操作时对笔法技术也提出了特别要求:单纯。基础训练包括笔画中实;线的内部运动直截爽劲而有异于金文大篆的顿挫涩行;毫尖刹那入纸露锋、藏锋、驻锋,不做过多的方向变化,收笔不宜一律悬针;分界线也可引入作品,但一定是书法的线;掺加草意而不作草笔……单纯非是简单,个性做好更不易,平时写楷书的积习不自觉地带入势必破坏这种单纯,丧失拙朴古意。二是拒绝变相异化。将古代杰作的某一隐晦局域幻灯放大,空间构成的精彩处理方式会使一类“前卫风格”的作品惭愧无地。后者之所以难能服人,症结在于:几乎所有致力于“前卫风格”(或称“现代派”)的书法工作者都未曾真正深入到书法传统的核心,对于拿来用作改造的“武器”(西方抽象画和西方现代哲学)亦顶多一知半解,有“打擦边球”的投机之嫌,在意识形态的现代文化方面普遍存在形而下的问题是有目共睹的①。
复审甲骨文拓片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启示,首要在意识上消解书体的概念与构字法的局限,甲骨文书法本体以及形式符号高度概括的草书(狂草)系统于此可谓著先鞭。解决了线的基本问题之后,再回到保持书体特征和保证文字可识辨性的把握中去。次者,新的书法空间形式探索必须审慎,力避陷入浅薄流俗。此外,个性艺术情趣和现代人文精神对于既有模式的扬弃与弥补,应该是严肃考虑的而非下意识的,否则不经意的一挥之间很可能对原本精华有所失察。在科学的方法 论面前,无视技术品位的理论家注定是空头的,妄自菲薄理论的创作家想必是匠气的,一切保守狭隘的成见皆不足为学问者训。
这是一个需要不断思考下去的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笔者抛砖于斯,且盼引玉为幸。
注释:
①从这个意义上严格来看,日本书法家手岛右卿那件闻名遐迩的墨象派作品《崩坏》也很难说是高层次的,它同弘一法师绝笔《悲欣交集》所展现的一种来自心灵至深处的动人毕竟不能等量齐观。
参考文献:
[1](荷兰)R.J.弗伯斯,E.J.狄克斯特霍伊斯.科学技术史.刘珺珺等译.北京:求实出版社,1985.
[2]邱振中.书法的形态与阐释.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
[3]陈爱民.甲骨文书法的艺术价值及艺术转换问题.艺术百家,2004,5.
[4]谭杰.感受:四川联合书法艺术学院专业教学.书法杂志,2004,5.
[5]王本兴.甲骨文拓片精选.天津: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05.
[6]徐振韬,周凤池.国际甲骨文书法篆刻家大辞典.香港:中华国际出版社,2000.
附:
西周金文书写风格的演变
金文是西周时期最重要的文字材料。其时,甲骨文已很少使用,简帛恐因材料的原因,保存到今天,也很成问题。因此,铸造在铜器上的文字成了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重要的原始文字材料。我们研究西周金文书写风格的演变,一方面对学习篆书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一方面对所载铭文铜器的断代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纵观中国书法的历史,在某一个时期,虽然也有少数作品与其时的大风格有所差异,但同一时期的绝大多数作品总是具有大致相似的书写风格,尤其是在书法艺术尚未自觉的西周时期。本文拟对西周金文不同时期书写风格以及演变的过程做一粗略的探讨。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我们在讨论西周金文书法风格演变之前,先来说明两个问题。
首先,商周之际完成了文字载体由甲骨向铜器的转变。众所周知,甲骨文的发掘出土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甲骨文一出土即受到学术界的推重。这成千上万片契刻文字的甲骨,为我们完整勾画出了商王世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虽然,盘庚迁殷之后的商墓中也有带铭文的铜器出土(盘庚迁殷之前的商墓中到目前为止尚无带铭文的铜器出土),但为数极少,且铭文大都是一两个字,为族徽或名称而已,只是到了殷末,才有几十字的铭文出现。现在发现的商代铜器,几十字的不超过十件,与甲骨文是无法匹敌的。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材料看,商代的最主要的“书写”方式是契刻,我们也清楚地发现,铜器上的文字风格明显是摹仿契刻的甲骨文而来,虽然当时已经出现了毛笔的书写。我们看殷末的铜器铭文和一些字体较大甲骨文,它们的风格几无二致。如有名的《宰丰骨》和《小臣俞尊》等。西周灭商之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甲骨文已很少使用,而在铜器上铸造铭文,不但迅速普及,而且单个铜器上的铭文字数也大量增加。武王时的重器《天亡簋》即有78字,成王时《何尊》有122字,到康王时已有近300字的《大盂鼎》出现,而后数百字的铜器,比比皆是。这种文字载体的转变,是当时社会政治生活的一种反映。我们从书法的角度来看,这可不仅仅是“书写”材料 的转变,它还隐含着文字“书写”方式的转变,在这之前的最主要的“书写”方式是契刻,之后最主要的“书写”方式则是铜器铸造,而铸造的前提是毛笔书写,铸造是对毛笔书写的再现。因此,我们也可以说,这时的主要书写方式是书写。那么,从书法的角度来看,就存在着从契刻风格向书写风格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在西周初期完成的。
其次,汉字有一个约定俗成的笔顺原则,在一个字当中先写哪一笔,再写哪一笔,或说是先横后竖,先撇后捺,先左边再右边这样的原则,这样的笔顺原则也是在完成上述转变的过程中形成的。在甲骨文时代,还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笔顺原则。虽然,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用墨写后契刻的甲骨,但是大多数的学者还是倾向于甲骨文是直接契刻的这一观点。在甲骨文的契刻过程中,一般是先刻出横画,然后再刻出竖画,或是先刻出竖画,然后再刻出横画。这是由特定的契刻方式决定的,很好理解。这在赵诚先生的《甲骨文字学纲要》里有详细的论述。由于是用刀契刻,笔画只能直来直去,不适合弯曲笔画的刻写。所以我们看到的商代甲骨文也好,金文也好,都是这种风格。不过,甲骨文是这种风格较好理解。殷代文字的这种特点,同样推之于同时代的金文中,这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了当时最主要的“书写”方式是契刻。我们现在还有幸可以看到商代的墨迹,墨书“祀”字陶片以及玉器上的朱书等,我们从墨迹中感受到的依然是那种和甲骨文、金文相类似的契刻风格。
丛文俊先生提出了“篆引”这个概念。我的理解,“篆引”的形成过程,就是文字由契刻风格向书写风格的转变,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我们上述的现在意义上的笔顺原则。契刻风格的消失,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入周之后,契刻风格的作品依然不少。只是程度在逐渐减轻罢了。契刻风格到书写风格的转变到西周中期才算彻底的完成。在这个转变过程中,还导致了铭文笔画由自然的书写状态向线条化的演变。为了表述方便,我们一般把西周分成早、中、晚三期。早期主要是武王、成王、康王、昭王,中期主要是穆王、共王、懿王、孝王,晚期是要是夷王、厉王、宣王、幽王。按照三代秦汉的制度,巫史卜祝之类专业性很强的职官和百工,都是家族世守不替的。武王灭商以后,很多的殷商原来的巫史卜祝及百工人员直接被纳入到周的政权中来,为周服务,这也是西周初期能延续殷商书风的直接原因。西周初期的铜器铭文存在两种书写风格。一类是殷商风格的延续。这一时期甚至还有完全契刻风格的作品出现。如成王时的《大保簋》即是如此,康王时期的《沈子它簋盖铭》也是殷商甲骨文风格的翻版。这类作品的特点是笔画的起止处显露锋芒,两头尖细,中间粗重就像是用毛笔直接画一条线呈现的那种自然状态,笔画也较为瘦削。这时大部分的作品用笔开始变的厚重起来,并且出现了起笔重顿的现象,弯曲的笔画也逐渐增加。这种风格由殷商的《小臣俞尊》《二祀 其壶》《四祀 其壶》等发展而来,西周初期,大量作品都是此类风格。如成王时的《刚劫卣》、《康侯簋》、《克 》、《保卣》、《叔方鼎》、《德方鼎》、《小臣单觯》等。有一些作品虽然不能确定它是哪一个王时期作品,但一望而知,为西周早期无疑,如《康侯鼎》、《 鼎》、《商卣》、《鲁侯尊》、《叔 父卣》等等。到康王时的《大盂鼎》把这种风格推向了一个高峰,也可以算是殷派书法的成熟之作。昭王时的《 觥》是《大盂鼎》风格的延续和升华。《 觥》在用笔上与《大盂鼎》相同,字形更见方正典雅,行气更加流贯,布局更加整齐,因而也显得更加精美。从上述不同时代作品的陈列中, 我们可以看出,殷派书风作品有笔法上由原先的两头尖细向着笔画逐渐厚实的方面发展,特别是起笔的尖细逐渐减少。但是笔画末尾尖细的频率还是很高。可以这样说,这种自然的书写状态在向粗细均匀的线条化发展。到西周中期,头尖尾细的尖尾部分开始泯灭,并且很快消失。
丛文俊先生说:恭王时期,“篆引”成为金文书法的唯一式样,某些旧式的肥笔已被改造成装饰性的圆点,其他偶有存留,也几如凤毛麟角。在这整齐划一的新秩序中,佳作触目皆是,品味之余,又很容易把它们忘记。(《中国书法史》)其实,这种变化从穆王时就已经开始了。如《静簋》《遹簋》《冬簋》,以及下面我们还要提到的著名的《班簋》。恭王时期的名作,当首推一九七六年出土的微氏家族器物群,他们创作了以《墙盘》为首的一大批有铭铜器,这些作品构成的时间序列正好显示着西周金文书法的发展状况。从《 觥》到《墙盘》,从《墙盘》到《 》组器物。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巫史卜祝及百工人员都是世守不替的,铜器制作即属此类。根据对器物群的综合研究,微氏家族七代人正好对应的是从武王到孝王,上面提到的这三组作品的用笔正是西周早、中期金文书法用笔的典范代表。《 觥》代表的是西周早期契刻风格向书写风格转化过程中的样式,《墙盘》代表的是契刻风格消失,书写风格确立之后的样式,也预示着未来书风发展的方向,《 》组器物代表的是西周成熟金文的样式。
西周金文从早期到中期的这种用笔的变化相当明显,而中期到晚期的变化则较轻微。随着到穆王、恭王时期“篆引”笔法的成熟,也开始出现了对自我风格的追求。正是孙过庭所谓的“既能平正,复归险绝”的追求。不知是历史的巧合,还是确有艺术上的先知先觉者。西周开国铜器武王克高所作的《利簋》和武王祭祀文王所作的《天亡簋》,也在冥冥之中预示着或说导引着历史发展的方向。丛文俊先生说此作品“已经暗示出未来的发展道路”。这两 件作品与西周初期的其它作品相比在风格上有所差异。这两件作品可以说没有受到殷末书风的影响,却有极明显的西周中、晚期的宗周之风。特别是《天亡簋》布局之自然、字体大小参差错落而不做作、浑然一体,远在《利簋》之上。和此二器作品类似的不多,有周公之子伯禽所做的《禽簋》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提到著名的《班簋》,郭沫若先生和吴其昌先生都定为是成王时器物,陈梦家先生先定为成王时器,后又改为康王时期。如果我们纯从文字的书写风格上来分析,它应当是《大盂鼎》之后而在《墙盘》之前的作品。因为《班簋》的笔法特点和《大盂鼎》一样,都是殷派书风,而字形比《大盂鼎》更见方正,整体布局也是秩序井然,上下成列,左右成行。因此唐兰先生定其为穆王时的作品。我们从对它书写风格的分析中也可以给以佐证。穆王、恭王时代之后,粗重的肥笔逐渐消失,原本很多斜向(相当于现代撇捺方向)的笔画变而为竖向和横向;笔画和笔画之间的连接也由原先的直接接触而而形成一些锐角形的情况,变而为由弯曲笔画的连接。我们还可以用以上的观点来对几件年代争议较大的器物略作分析。
《宗周钟》郭沫若先生和吴其昌先生定为昭王时作品,唐兰先生定为厉王的作品,年代差别很大。我们分析一下它的用笔物点,尖笔已消失,笔画弯曲处,自然流畅,篆引笔法已相当成熟;从布局上看,上下成列,左右成行,单个字形方方正正,追求整齐划一的美。从这些特点来看,它完全符合西周晚期金文书法的特点。因此,唐兰先生定为厉王的作品应当说较为恰当。
我们再来说一下有名的《毛公鼎》,郭沫若先生定为成王时的作品,而大多学者定为宣王时作品,年代相差也很大。单从书法上看,成王时期不可能出现如此体大思精的作品,成王时期,大多作品还在殷派书风的淹盖之下,笔法也是头尖尾细,字数较多的作品,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大约只有《何尊》,字数已过百,但布局却稍嫌粗糙,用笔还是篆引形成之前的殷风时期的厚实风格,虽也瑰奇动人,西周后期的作品相比,不论是笔法,还是结构章法都很拙劣。而《毛公鼎》笔法之精巧熟练,结构之精美,章法布局之奇巧构思,这种种特点都表明它为西周晚期之作,把它放到西周晚期的作品中,是比较恰当的。下面我们主要来分析字形及章法布局的演变。
我们从对大量作品分析后得到如下结论:西周早期的字形多属于不规则型,并且字的大小不一,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字的外形由不规则型向方型在逐渐演变,并且字的外形的大小也逐渐求得大小一致,到康王时候的《大盂鼎》算是这种风气的成熟。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上下成列,左右成行,整体布局整齐划一的作品就是在康王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单个字的结构布置,和铭文通篇的整体布局是同步演进的。随着单字结构的越来越方正,整体布局也越来越整齐划一。
西周中期,过百字的作品大量出现,但是极少有左右不成行者,此时殷风消失、西周金文高度成熟。到懿王、孝王时期,出现了大量精美之作。如《谏簋》、《南宫柳鼎》、《元年师兑簋 》、《三年师兑簋》、《师酉簋》、《舀鼎》等等,类同的作品还相当多。由于用笔结字技巧的高度成熟,更精微的变化也孕育在其中,为追求不同的艺术个性提供了条件。可以这样说,西周早期书写风格主要是在用笔上的演进,而西周中晚期书写风格却是在单字结构以及章法布局上的演进。
西周晚期,仍延续着整齐划一的追求,“篆引”笔法已圆转自如。如夷王时的《休盘》、《颂鼎》、《颂壶》带阳文界格的《大克鼎》等,还有厉王时的《史颂鼎》、《宗周钟》、《 簋》等。懿王时期的《舀鼎》,为记事作品中的典范。文分三节,互不相关。作品一如毛笔书写而成,笔锋显露,行气如贯,和同时的其它作品有异,它显示的是手写的状态,可以算是西周金文中的熟练的手写体。在这里,我们不能不再提到微氏家族的《 》组作品。现在普遍认为它们是属于孝王、懿王时期的作品。有《 钟》《四年 须》《 簋》等。它们的“篆引”笔法已很完美。它们出现的风格差异主要体现在单字结构和整体的章法布局上。《 钟》的单字结构是极力外撑,线条的运动幅度是大开大合,显得大气而有魄力。这一段文字就是《墙盘》的第一节,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和《墙盘》进行对比,《 钟》的线条比《墙盘》更加圆熟,字形更显方正。《四年 须》体势平和,用笔短促,以柔媚见长。《 簋》拉长竖画,使字形变得修长,圆转自如,书风雄秀。
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厉王时期的《散氏盘》,《散氏盘》的风格与当时其它的作品迥异,而出于时风之外。根据研究书法史的经验,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存在在着规范正体字和手写体字并存的局面。如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上的字体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当时的墨迹相比,我们再把秦汉刻石和我们现在能看到的竹木简帛相比,不难看出规范正体和手写体的巨大差异,规范正体用于铜器、碑石之上,手写体用于日常书写之时,但也偶有相混,如汉之《石门颂》,没看到汉简之前,我们诧异于它的风格乞求,汉简出土之后,我们大解,那是当时很平常的手写体,而其余汉碑,则是用的当时的规范正体。《散氏盘》即是这种情况。近见《文物》刊《柞伯鼎》与《散氏盘》风格相当接近,也为同时之器物。
近年出土的单氏家族的《来盘》等作品,为宣王时期器物。它是目前所能见的盘铭中字数最多者,和《墙盘》一样,不光在文献上具有极重要的价值,在书法上也是西周中期和晚期是典范的作品。《来盘》是西周金文中单字结构和整体布局最整齐划一者,它的线条粗细均匀,结构极力追求方正,它开启了后世小篆的书写风格。同时也出现了西周金文中最具艺术魅力的《虢季子白盘》。它和《毛公鼎》一样,都是宣王时期的作品,之所以说它是最具艺术魅力,一是它的结构,一是它的章法布局。它虽然也在追求方正,但是,它在追求方正的同时,结构紧结,每一个字都向自已的中心收缩,而很多的笔画又向四方极力的伸展,呈现出辅射状,而它的章法布局则追求疏朗有致、顾盼有情的姿态,非常具有艺术魅力。是金文书法成熟之后能追求自我艺术风格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