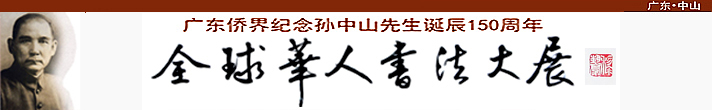“东西贯中——吴冠中艺术回顾大展”举办前夕,吴冠中长子吴可雨将父亲的《云南行》速写48图和手稿3篇捐赠给浙江美术馆永久收藏。
11月22日上午,吴可雨在浙江美术馆的咖啡厅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问:我们从电视屏幕上,从吴冠中先生的图书、作品当中,可以感觉到他是一个严肃的人。他平常说话多不多?
吴可雨:他的气质是典型的艺术家的气质,说话多不多看谈什么。你如果谈艺术,他的话就特别多,你问他一个问题,他就会滔滔不绝地说很多;如果不谈艺术,他的话就很少。
他是以他的为人处世之道、他的人生标准来要求我们,他跟我们讲道理的时候并不多,身教胜于言教,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对我们就是最好的教育。
问:你后来去了新加坡,以前和父亲在一起的时间多吗?
吴可雨:多。我3岁时,父亲从法国留学回国,在北京工作,当时我和母亲住在父亲老家宜兴,后来把我们接到北京。从3岁起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我下乡插队到内蒙古5年,父亲去农村劳动,分开过一段时间),我一直和父母一起住。那时候家里的条件很差,我们都挤在一个大杂院里。1990年我去新加坡之后,经常回北京看父母。
问:你在开幕式上说,父亲很多年在简陋的条件下画画,家里地方小,很多大画都是绕着桌子画的。当年你们的住所是怎样的?
吴可雨:1982年之前,我们一家住在靠近什刹海的一个大杂院里,院子里住了50多户人家,我们有两间屋子,外屋是我、两个弟弟住,里屋是我爸妈住。屋子里不是水泥地,而是土地,因为靠近什刹海,地很潮,那时候都穿布鞋,鞋子放在地上一晚上,第二天早上鞋底都是湿的。我们家的家具非常简陋,都是木头桌子、凳子,因为潮湿,时间长了,木头腿都烂了。窗棱上夏天粘一层纱布防蚊子,冬天糊一层高丽纸,自己拉煤、生炉子,也不暖和,非常冷。外屋有一个书桌,一个旧沙发,中间摆着一个很旧的画架子,就占那么小一块地方,画大幅的油画要离远一点看效果,父亲就出门隔着窗户看,看完了再进来画。我们在大杂院里住了25年,父亲画了很多精彩的作品。今天的人们可能难以想象,他是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创作的。
父亲晚年住在方庄,工作条件已经得到很大的改善,虽然面积小,总算有画室了。现在一些画家住在大别墅里,有大画室。很多人看到我父亲现在的创作和生活条件,都觉得不可思议。我父亲的一生是追求艺术的一生,他对于物质没有很高的要求。过去是政治的压力,现在是金钱的诱惑,不管是什么样的条件,他都不变,保持着艺术家的本色。
问:他为什么没让你们学画画?
吴可雨:很多人都问过这个问题。现在人们看到他地位很高,画价很高,但很多人不知道他这一生是怎么走过来的。30多年前,或者再往前追溯一下,那个时候中国的社会环境完全是政治决定一切,强调文艺要为政治服务、为阶级斗争服务,那种环境根本不能发展艺术。特别是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尽管抱着满腔的热情回国,想为新中国的艺术事业做出贡献,但是他的理想和当时的政治环境格格不入。他在法国巴黎学的是西方艺术,他的艺术观被认为是资产阶级的,是腐朽的,他的文艺思想和创作在当时是容不得的,所以他只能一直忍着。后来他在中央美院受排斥,到了清华美院,很多年里被边缘化、被压制、被批判。
他说过,他自己走上艺术道路,完全是因为他热爱艺术。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他一直在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但是走上这条道路之后,他发现从事艺术是没有出路的,他不愿意我们再走这条路。我们小时候也喜欢画点画,他就说,艺术有什么用呢?做“空头艺术家”没有意义,让我们做一些对人类有实际意义的工作。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他坚持画画,但是没有展出、出版的机会。因为那时候都画工农兵、歌颂领袖,你画风景,画资产阶级那些东西,根本就为社会所不容。所以他是反对我们学画的,这也是因为他自己惨痛经历的教训。
问:您的母亲至今不知道父亲已经离开?
吴可雨:对,还没告诉她,因为她身体情况不好,怕她知道后,精神上受不了这个打击,加重她的病情。她现在有一点老年痴呆症,不是很严重,但是在思考问题这方面,她已经不是正常思维了,而且记忆基本没有了。比如你跟她说今天的事情,她一会儿就忘了。她非常关心爸爸,已经形成习惯了。所以,吃饭的时候会问:“爸爸怎么还没回来吃饭呢?”晚上又问:“爸爸怎么还没回来睡觉呢?”我们就骗她说爸爸身体不好,还在医院休养,她就信了。第二天她仍然会问。现在母亲身边离不开人,我和弟弟每个人轮流陪她一个月。本报记者 续鸿明
稿源: 中国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