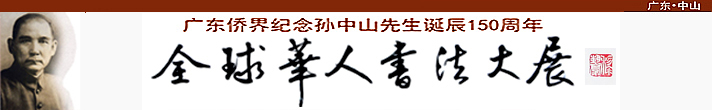一生,成就一部中国现代美术史;一人,开辟一条独特的美的历程。从早年弄潮于艺术运动的波峰浪谷,成为一位狂飙突进式的领军先驱;到五十年面壁潜修,孤独求索,探寻出中西调和的绘画新径;直至秋霜红叶,实至名归,成为一代开宗立派的艺术宗师——林风眠,以自己跌宕起伏、波澜壮阔的一生,完成了一个现代艺术殉道者的使命,也使后人读到了一部凄婉而苦涩的诗意人生的传奇。
游学异国,重新发现东方艺术
1900年11月22日,林风眠出生在广东省梅县白宫镇阁公岭村一个石匠家庭。幼年的林风眠时常跟着祖父林维仁上山打石头,林风眠的父亲林雨农也是石匠。不过,除了会刻石头外,父亲还能在纸上做画。或许正是这一点点改变,使这个石匠之家的后代最终舍弃了石头而迷上了画纸,小小年纪就开始翻弄《芥子园画谱》,几年工夫就画得像模像样了。
15岁时,林风眠考取了省立梅州中学,他早熟的画才立即得到美术教师梁伯聪的赞赏。他发现林风眠对形象有着超强的记忆力,并且善于发挥和创造。1919年7月,林风眠中学毕业了,恰好此时他收到了梅州中学的同窗好友林文铮从上海发来的信函,告知他留法勤工俭学的消息。于是,林风眠怀着对欧洲艺术的美好憧憬,告别家人前往上海,和林文铮结伴登上了法国邮轮奥德雷纳蓬(Andre le Bon)号,作为第六批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踏上了注定要改变其一生的欧洲求学之路。
1921年,林风眠转入法国国立第戎美术学院,正式开始美术专业的学习。不到半年,林风眠的绘画才华就被校长耶西斯发现了。在耶西斯的推荐下,林风眠又转入法国国立高等美术学院,进入被时人誉为“最学院派的画家”的哥罗蒙画室就读。林风眠一来到这个学院派的“老巢”,就完全沉迷于细致的写实主义学院派画风之中——这种选择,有其主观因素,如林风眠所说:“自己是中国人,到法后想多学些中国所没有的东西,所以学西洋画很用功,素描画得很细致。当时最喜爱画细致写实的东西,到博物馆去也最喜欢看细致写实的画。”另一方面,这种选择也与当时的时代风潮有着必然的联系。五四前后,对中国画改良的呼声此起彼伏,先是康有为喟叹“我国画疏浅,远不如之,此事亦当变法!”接着五四悍将陈独秀又发出“改良中国画”的惊世之音。而他们所主张的变法方向却是惊人的一致,那就是康有为所说的,要“取欧画写形之精,以补吾国之短”,也就是陈独秀所主张的,“要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的写实精神。”林风眠是一路紧随着五四新潮走出国门的,自然深受其观念的影响,初进艺术学府,一度醉心于西方写实的古典传统是毫不奇怪的。这既是打好绘画基本功之必需,更是当时世风浸染的必然结果。
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个爱才的耶西斯校长又跑过来给了林风眠一记“当头棒喝”——那天,耶西斯专程来巴黎看望这位得意弟子,他发现林风眠正无比认真地研习西方学院派写实画风,立即毫不客气地批评他说:“你是一个中国人,你可知道,你们中国的艺术有多么宝贵、优秀的传统啊!你怎么不去好好学习呢?去吧,走出学院的大门,到东方博物馆、陶瓷博物馆去,到那富饶的宝藏中去挖掘吧!”他还告诫这位中国学生:“你要作一个画家就不能光学绘画,美术部门中的雕塑、陶瓷、木刻、工艺——什么都应该学习。要像蜜蜂一样,从各种花朵中吸取精华,才能酿出甜蜜来。”这番话,对林风眠来说恰如醍醐灌顶,使他从对西方古典画风的沉迷中猛醒,重新发现了“东方艺术”的魅力。
这次对东方艺术的“重新发现”,对林风眠一生的艺术走向影响深远。在他后来的众多杰作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各种传统艺术和民间艺术对他的直接影响,林风眠九十岁时谈到自己的艺术时曾坦言:“我的仕女画最主要是接受来自中国的陶瓷艺术,我喜欢唐宋的陶瓷,尤其是宋瓷,受官窑、龙泉窑那种透明颜色的影响。”而这一改变,正是从耶西斯校长那“一声棒喝”发端的。
归国任教,艺术救国接连失败
1923年春天,在同乡熊君锐的邀请下,林风眠与李金发、林文铮等同窗好友开始为期近一年的德国游学。这一年的游学生涯对林风眠具有特殊的意义。在德国游学的一年,他的创作时间相对宽裕,这使他充分接触到当时最为新锐的艺术流派,如表现主义、抽象主义等。尤其是以德国为中心产生的“青骑士”画派,令林风眠心灵为之震撼。回到法国之后,林风眠与几位趣味相投的艺友发起组织了一个绘画沙龙组织——“霍普斯会”,“霍普斯”指的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阿波罗在神话中主宰光明、青春和艺术,林风眠以此命名,正表现出他决心为世人创造有青春活力的艺术的坚定信念。1924年2月,“霍普斯会”联合另一个旅法艺术团体——美术工学社,要在法国的斯特拉斯堡举办一次中国美术展览会,正巧,当时中国教育泰斗蔡元培先生正旅居斯特拉斯堡,组委会就特邀他为名誉会长。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中国古代和现代艺术展览会”于5月21日正式开幕,一时之间,“巴黎各大报,几无不登载其事”。林风眠在此次展览中,推出了包括14幅油画和28幅彩墨画在内共计42幅作品,被法国《东方杂志》誉为“中国留学美术者的第一人。”
蔡元培先生在参观展览时,被林风眠的一幅展品深深吸引,那就是他游学德国时所作的《摸索》。这是56岁的蔡元培与不满24岁的林风眠的第一次相遇,正是这次不寻常的相遇,改变了林风眠此后的艺术人生。
蔡元培先生对林风眠的赏识,很快就变成了一种能量巨大的助推力量,牵引着林风眠从西方转回东方。1926年,由于德高望重的蔡元培先生鼎力推荐,加上前期回国的同窗好友王代之的大力助选,远在欧洲的林风眠竟然以得票第一而被任命为国立北京艺专校长——据说,这是当时全世界最年轻的艺术院校校长。
1926年早春,26岁的林风眠乘船回国。1926年3月1日,林风眠进京赴任了。作为“调和中西艺术”的具体措施之一,林风眠使出了两个奇招:一是把木匠出身的“乡巴佬”齐白石请进艺术殿堂任教,二是从法国请来名画家克罗多(Claudot)来校讲学。显然,林风眠是要把齐白石的传统国画与民间色彩,克罗多的新印象主义画风一并注入中国绘画教学,从而培养出第一批实践“中西融合”艺术理想的新生力量。
然而,他的努力并不顺利。齐白石的到来引发了一些国画教授的抵制,有人扬言:“齐白石从前门进来,我们从后门离开”,大有与之势不两立的意味;而克罗多提出展览会要取消中西绘画界限的建议被林风眠采纳之后,同样遭到众多画家的反对。不过,年轻气盛的林风眠不为所动,坚持强力推行自己的艺术主张。1927年5月11日,林风眠发起并组织的“北京艺术大会”在北京国立艺专开幕了。此次展览的2000多件展品第一次以不分中西的混合陈列方式展出。这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一次艺术大展。按照林风眠的设想,这次大展要仿照法国沙龙,成立审查委员会评选作品。但终因画界门户之见太深而被迫取消,这使他的“艺术运动”从一开始就打了折扣。
在内外交困的境遇中,北京艺专是无法再干下去了。是年7月,林风眠愤然辞职。1927年9月,接受蔡元培的邀请,林风眠南下南京就任中华民国大学院艺术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同年年底,受委托筹办“国立艺术大学”;随后,蔡元培在杭州西湖之畔选定了民国政府的最高美术学院——国立艺术院的校址,接着,林风眠被任命为校长兼教授。这是林风眠得到的又一次实现“艺术救国”理想的良机。
1928年4月8日,国立艺术院(1929年改名为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蔡元培亲自到会祝贺并发表了讲话,再次阐述了“以美育代宗教”的观念。林风眠无疑是蔡元培这套美育理念的忠实实践者,在国立艺术院组织法中明确指出:“本院以培养专门艺术人才,倡导艺术运动,促进社会美育为宗旨。”在杭州艺专的教育方针中,则体现了林风眠的一贯主张:“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
然而,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总会在不经意间悄然袭来,令林风眠进退维谷。在杭州艺专的发展历程中,有两件事是不能回避的。一件是林风眠与潘天寿的中西画系分合之争,另一件则是“西湖一八艺社”的分裂。
关于林潘的这次艺术争论,缘自林风眠依照“调和中西”的设想,提出要把国画系与西画系合并的动议。对于一直以“调和中西艺术”为己任的林风眠而言,只要能创造出时代新艺术,并达到通过新艺术来改造社会的目的,那就无所谓中西。而潘天寿则持相左意见,他认为东西绘画体系就如同两座独立的大山,两座大山间,可以互取所长互相沟通,但如果随便吸收的话,则只能是各取所短。
相形之下,“西湖一八艺社”的分裂则更具有历史的典型意义。建校之后,林风眠在创建“艺术运动社”的同时,也支持学生自发结社,讨论学术问题。于是,各种学生社团纷纷建立,“西湖一八艺社”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个。1930年春天,“西湖一八艺社”在上海举行首次公开展览,在展后举行的座谈会上,许幸之大力倡导“普罗”美术,并推重“为人生的艺术”这一富于时代特色的口号。而另一部分社员立即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普罗”美术的提法,违背了林校长倡导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宗旨。这场争论的激烈程度远远超过了林潘二人的学术之争,最终导致“西湖一八艺社”的分裂——一部分拥护“普罗”美术的社员,删掉了“西湖”二字,以“一八艺社”的旗号加入了鲁迅在上海刚刚掀起的左翼美术运动。这对林风眠在学校所倡导的“艺术至上”观念,客观上不能不说是一次不小的冲击。
渐渐的,人们发现一度激情四溢的林风眠校长开始变得沉默了,对于分裂出去的“一八学社”,他既不支持、亦不反对,采取一种放任自流的态度,这反映出林风眠在政治与艺术关系问题上,陷入了困惑和迷茫。他的注意力也逐渐从过去致力于艺术改造社会的运动,逐渐转移到绘画艺术的探索和变革上来。
退回画室,亲身实践“调和中西”
当林风眠从一个艺术运动的领袖回归到一个画家和教育家的时候,他的心态立即变得平和而冲融。应该说,在杭州艺专的十年,是林风眠一生中最优裕也最安逸的一段时间。
在这十年间,林风眠的艺术创作也收获颇丰。他开始亲手尝试“调和中西”的艺术设想,油画中融进中国元素,水墨中掺入西画构成。他还画出一批直接反映民间疾苦的大幅作品,如《人道》、《民间》、《痛苦》、《斗争》等,引起了社会上强烈的反响,也招致了一些非议和不满。
在此期间,中国画坛上还发生了几次激烈的艺术观念论战,其中尤以徐悲鸿与刘海粟的激辩最为轰动,一方站在西方古典主义的立场,猛烈抨击西方现代艺术;另一方则祭起西方现代派的大旗,与其展开对攻。而作为中间路线的代表,林风眠的“调和论”自然也无法超然事外,时常被牵扯到论战的漩涡中,一会儿成为某一方攻击的靶子,一会儿又被某一方引为同盟。在纷乱的喧嚣中,林风眠备受困扰。他已经不再像十年前那样喜欢争先弄潮,也消解了争当领袖的锐气和雄心,他只想退回画室,在画布和宣纸上去“调和中西”。
然而,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的全面爆发,把林风眠潜心艺术的梦想击碎了。1938年,教育当局下令,将杭州艺专与同样南下避难的北京艺专合并,成立抗战时期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这两所学校林风眠都担任过校长,然而,今非昔比,物是人非,多年来的矛盾纠结在一起,使两校合并成为一个摩擦与碰撞的爆发点。在经历了两次“倒林”风波之后,林风眠再也无法忍受这些烦人纠缠,他递交了辞呈,怅然地离开了国立艺专。
如果说,十年前从北京艺专辞职,林风眠雄心犹在,时刻准备东山再起的话,那么,此次从国立艺专辞职,他已经心灰意冷,“艺术救国”的理想完全破灭了,当年的激情也只剩下一丝余温,那就是 “以身试法”去追逐一个“调和中西”的绘画之梦——这成了林风眠内心仅存的艺术理想——为了实现这个艺术宏愿,他不惜单枪匹马、孤军奋战,以一己之力去改写中国绘画史,他要用自己的艺术实践和绘画作品向世界证明:“我林风眠倡导的道路不但是行得通的,而且是一条宽广的新路!”
标领时会,终成一代宗师
林风眠从国立艺专隐退后,并没有选择文艺界人士相对集中的重庆北碚一带居住,却跑到嘉陵江南岸一个大佛殿附近租了一间旧泥房,离群索居,专事绘画。从1938年至1991年,整整53年的漫长光阴,林风眠始终作着寂寞的艺术探索。这期间包括了重庆时期(1938-1945)、杭州时期(1945-1951)、上海时期(1951-1977)和香港时期(1977-1991年)。对这四个时期绘画风格的演进和变化,众多艺术史家已经做了精细的分析和精当的评述。概言之,林风眠自重庆退隐之后,绘画题材主要转为风景、仕女、禽鸟、花卉、静物和舞台人物,对现实人世的描绘越来越少,对自然和虚幻人物情境的描绘日渐增多;作品的色调逐渐明朗,情绪转为平和;油画越来越少,水墨和彩墨成为主要形式;激越的呐喊和沉重的悲哀转换为宁静的遐思和丰富多彩的抒写。绘画艺术日益成为林风眠抒发和展现生命本体的手段,画家的情绪与大自然的生命日渐融合,两者共同编织着一个个真善美的梦境。
宣纸,毛笔、线条,这些中国画最重要的工具,标志着画家的文化执着;而色彩、造型、构成,却是显而易见的西方范式。林风眠在寻找一种新的绘画语言,寻找自古未有的表现形式,来改造传统的中国画,抑或是在创造一种新的中国画。“方纸布阵”,这本身就是自设的一个困局;不再留白,至少是不刻意留白,一举颠覆了中国传统美学里“计白当黑”的铁律;线条不再成为“笔墨”的载体,而纯化为造型的工具,这就从本质上动摇了线条在国画中的美学地位。林风眠在九十岁时曾有一段独特的“论线条”的谈话:“我是比较画中国的线条。”他说,“后来,我总是想法子把毛笔画得像铅笔一样的线条,用铅笔画线条画得很细,用毛笔来画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东西练了很久,这种线条有点像唐代铁线描、游丝描,一条线下来,比较流利地,有点像西洋画稿子、速写,我是用毛笔来画的。”(见《林风眠台北答客问》)这番“夫子自道”,仿佛勾勒出林风眠在“一条线”上如何来“调和中西”——前提是“我是画中国的线条”,中间经过吸取中西艺术的营养(西方的“铅笔线条”和唐代的“铁线描”和“游丝描”),加之“练了很久”的努力尝试,终于达到了最后的效果:“有点像西洋画稿子、速写”,但是,这却是“用毛笔来画的!”
林风眠借鉴西方艺术也有独到的取舍。他先是由西方古典主义入门,转而醉心于印象派、野兽派乃至立体派等西方现代艺术思潮。林风眠看到这些西方现代派艺术,或多或少都从东方艺术中汲取过营养,因而他觉得现代派似乎更容易切入中国绘画。同时,林风眠的留学时间大多消磨在东方博物馆的陶瓷作品上,这也成为他改造中国画的民间底蕴。在林风眠的作品中,黑色往往被当作一种色彩来运用,而不再被当做“墨分五色”来看待。这样一来,他的作品从外观上看确实不像传统中国画而更像西方画。但是,如果透过形式去分析一下作品的精神内涵,那种凝聚在尺幅中间的悲剧情怀,那种不必凭借题诗和书法就自然而然扑面而来的浓郁诗意,却使画面上的文化意蕴得到了升华,使之更为契合中国画作为“心画”和“诗画”的特性。林风眠耗尽半生心血和才智创造出来的“风眠体”绘画,从面世之日就饱受争议,林风眠也曾一度为自己的绘画算不算中国画而苦恼。但是,他从来没有动摇自己的艺术信念,也没有停止自己的艺术探索。如今,大师已去,画风犹存。历史已经证明,林风眠在当代绘画史上开辟了一个迥异于任何人的新体系,他关于中西融合的观点以及对诸如形式、材料等问题的关注,极大地丰富了20世纪中国绘画的创作面貌,对后来者具有渡世金针的作用——如今,“方形布阵”的中国画早已司空见惯,而“风眠体”的后继者更是比肩接踵,绵延不绝,且名家辈出,风靡世界。林风眠也由此成为世人公认的标领时会,开资后学的一代宗师。
在林风眠九十岁时,有一位香港实业家提出要捐款为林风眠建立纪念馆。这本是每一个艺术家都梦寐以求的终生志业,而林风眠老人却淡然地谢绝了,他将这笔巨款捐给了中国美术学院(其前身即杭州艺专),设立“永芳艺术基金”。这一年,在北京和台北分别举办了林风眠九十诞辰大型回顾展,年底,这个展览终于回到了林风眠的故乡广东梅州——家乡父老对这位从19岁离家就再没有回来的游子的作品,给予了最热诚的欢迎,就像迎接一位凯旋故里的英雄。
1991年8月12日,91岁的林风眠在香港溘然长逝。由此,中国现代美术史有了一个新的标识:在林风眠以后,中国绘画的整体格局已经与林风眠之前迥然不同了。
文章来源: 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