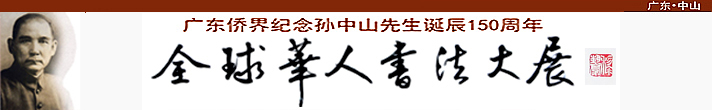许多年前有人喊国画死了,哭地像孩子一样悲伤绝望,其实不过是把自身悟性的穷途哭成了群体意识的悲怆,想来还是有些铮铮之气的。可惜后来朱德群,赵无极的成功让之前的“国画之死”变成了虚话,他们的成功也绝非仅仅局限于海外的传播,或者画的画框里,当优质的欧洲印象意识与优质的东方写意融在一起时,所触发的美往往会是一种新笋乍破而又似曾相识的味道。阅读者的扩张散漫和美学的集中凝神不可思议的结合在了一起,好似植物学上的嫁接生出的奇花异果,而那名嫁接的园丁,恰是风眠先生。
在林风眠之前,得感谢一个法国人——耶希斯,这位国立美术学院院长有一颗共和的心。他告诉林风眠的话大意是这样的:“你是一个中国人,你们中国的传统艺术是多么宝贵,多么美……你是一个画家,就不能光学绘画……”真是一辈子的良言。大概人之无私人之审美的通和尽在于此,在那个政治波动国情弱小的年代这样的赏识让人尊敬。这位耶希斯先生让我想起了张伯驹,大约所有妙人都具备了上上智,而衍生的了了心。这番话后来被印证确是点破林风眠的顿机,津渡灯塔一般。
只是后来的风眠先生太悲凉,当房产商书画商把他的价值一再用金钱叠高时,那些悲凉被那些身后的隆重轻轻湮没,谈起林风眠时不是说他是最年轻的国立美院院长,就是孤鹜野蒿的肃杀,或者富士比、嘉德的一路走高。这些话题原不属于他,真实的他后来是患着丧妻丧子故乡不能回的哀愁的。她的母亲被僻陋的乡人挫了骨扬了灰,那个小小的梅县曾经是容不得自由的爱情的,这痛根及到了风眠先生的灵魂深处,是任何愧疚都不能抚平的。那些低眉淡目丰腴的仕女,看似从晚唐的诗意中从来,而能说服人心的,大约也仅仅只有怀念。风眠先生一直保存着罗拉的镜心小照,几次搬家都不曾遗弃,这样的静物在于一朵,一束花的冷搁下别是一般滋味。很多静物后来确是独白了,也许无关灵魂的,但那是一种浸淫的思想姿态,花开让人沉默。
风眠先生说自己是“好色之徒”,此色先窄意地解为颜色,色彩原本在国画里是被忽略的,中国画讲究点、线、墨并且追求技术以外的东西。如今我们看凡高、马蒂斯,尤托利罗却是用了色眼,毕竟灵魂是抽象的,是属于一个画家的整体,而分散开来,色彩的眩目所构成的内心烂漫却是收在眼中的。藤黄是风眠先生孤标独特的地方,这种佛家的颜色在风眠先生的后期竟是揉捏的游刃有余。佛家有冰雪,有冷酷也有生命循环的大慈悲,后来风眠先生是否悟得我们也将不再知晓。
艺术轻的时候只是雏鸡的一根羽毛。在那个混乱的文化大革命的年代里,美艺像是“毒蛇猛兽”,惟有热情是“正经”。风眠先生也被打入了“黑画家”,一直想避开这段不提,但不知觉就把这些荒唐抖开,那些窒息人性的枷锁扣在诸多天真的艺术家身上,小孩变成大人,大人变成小孩的闹剧又让风眠先生的灵魂受伤,他后来去了巴西最后定居在了香港,居然不是杭州,不是重庆,不是广东梅县。好在那时有周总理,这位有着仁人之心高蹈情怀的总理无数次出现在艺术家真危难的时刻,风眠先生亦是他特赦的。后来总理之死,风眠先生便是哭得最伤心的那一群。
美学学术教育上时常翻风眠先生的册子,有段大意如是:真正的艺术家是蝴蝶,初期是虫,然后要给自己做茧,最后要有从茧里冲出的勇气。足以时常念叨回味。而他的美学核心“中西合璧”将给绘画带去生的力量,从这个世纪开始并将发展成诸多流派,他的高足们也将桃李四方自我争妍,当初那个嫁接的手如今变成了基因,它将构成绘画的种种只等真正的艺术家去开启。那些远去的故事,犹如秋来雁南飞时水衢陂塘边的瘦黄的芦苇,在北风里吹地如儿时短笛,是让人不愿遗忘的回忆。(作者:疏约 )